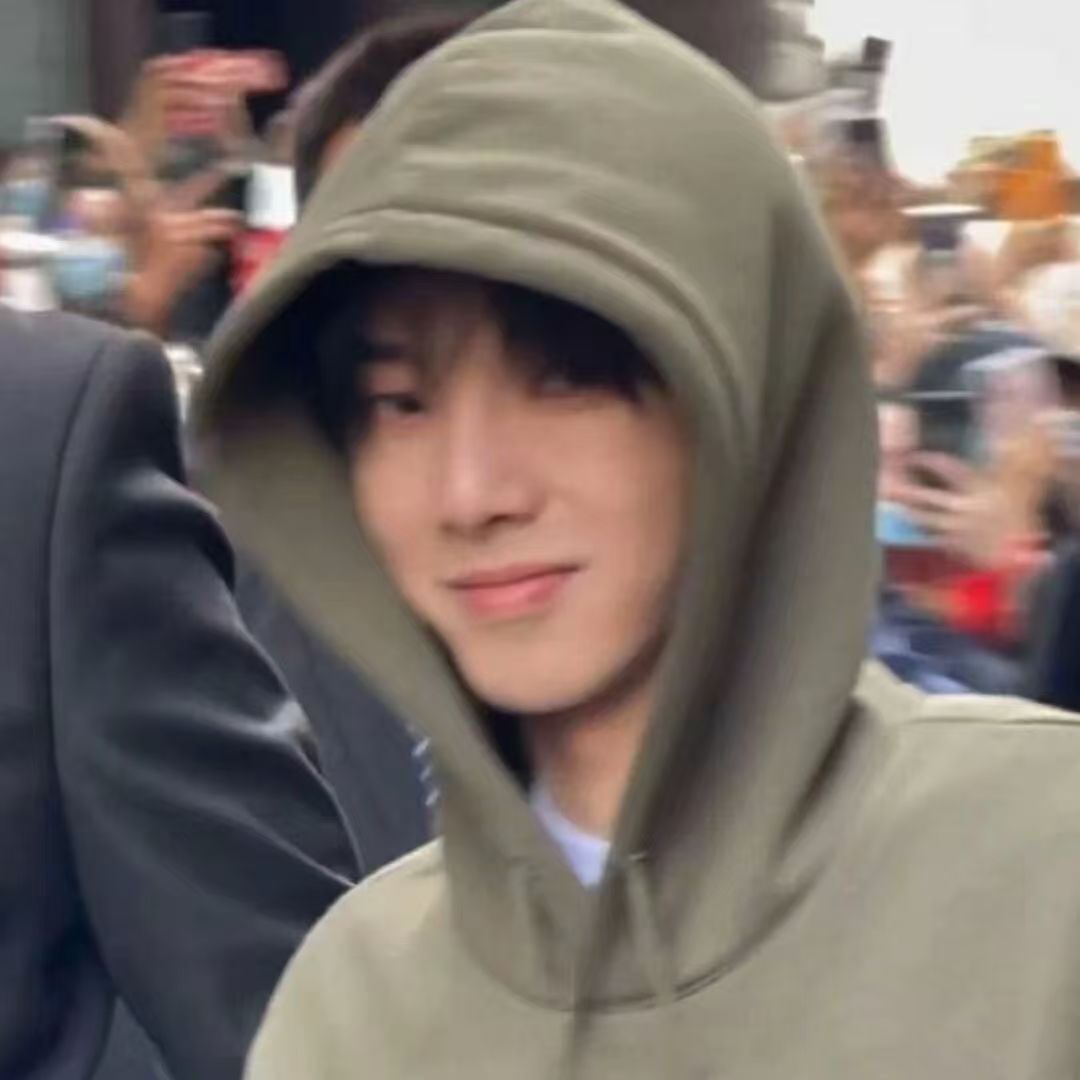《泥潭》在历史与人性的迷雾中寻找星光
翻开刘楚昕的《泥潭》,扉页上那句 “迷失在黑夜中时,不妨抬头看看星空;如果不知道该相信什么,人应当面对自己的良知” 像一束光,突然刺破了历史的阴翳。这部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小说,用亡灵的呓语、编辑的拼图、“奇人” 的回望,搭建起一个关于挣扎与救赎的叙事迷宫。而那些散落在字里行间的金句,恰似泥潭中闪烁的星光 —— 既是对个体命运的叩问,也是对历史本质的沉思。
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,但回头想想,都是传奇
这句话出自刘楚昕在漓江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哽咽感言,却像一条隐秘的线索,串联起小说与现实的双重人生。小说中,没落旗人恒丰在亡灵视角下回望一生:父亲自尽、妹妹失散、自己被乱枪打死,“像被踩死的毛虫一样蜷着身子”。他的痛苦是具体的 —— 下颌骨碎裂时的温热血流,被巡警用枪托杵肚子的屈辱,以及对 “连死亡日期都记不清” 的荒诞。但当这些碎片在记忆中重组,恒丰的挣扎却成了一面镜子:历史从不是宏大叙事的平滑直线,而是无数个体痛苦的集合,是 “被侮辱与被损害者” 用血肉写就的传奇。
刘楚昕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?从 13 岁萌生作家梦,到 34 岁凭《泥潭》获奖,中间是 “投稿被拒十多年” 的沉寂,是女友患癌去世的重创,是 “博士毕业后在家躺了三年” 的迷茫。他在签售会上自嘲 “名气大于实力”,却也坦言:“痛苦不必用来兑换勋章,但若注定深陷泥潭,就在淤土里种出莲花。” 当小说中关仲卿从革命理想的幻灭中重新站起,当神父马修德在战火中坚持记录日记,这些人物的 “传奇”,与刘楚昕在书桌前删改 50 万字初稿的固执,本质上并无不同 ——所谓传奇,不过是把 “挺过去” 三个字,写成了生命的注脚。
泥潭的可怕,不在于它的肮脏和黏稠,而在于它的吞噬力
“泥潭” 是小说最核心的隐喻,刘楚昕曾阐释其三重内涵:致敬李劼人《死水微澜》的历史厚重,暗喻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,更映射自身 “越挣扎越深陷” 的创作困境。书中,荆州古城黄金堂与天桥的分割线,既是满汉民族的物理界限,也是阶层固化的象征 —— 旗人八十四年轻时为饱腹替人打架,老了沦为乞丐,“别人啐他、打他,他笑;从恶狗嘴里抢来一点饭菜,他还笑”。他的笑不是麻木,而是被泥潭吞噬后的生存本能:当反抗变得徒劳,“活着” 本身就成了最卑微的抵抗。
这种吞噬力在革命爆发时达到顶峰:恒丰的父亲恒龄作为守城将领,在 “杀革命党” 与 “保百姓” 间进退两难,最终举枪自尽;关仲卿卧底清军时,目睹昔日同志屠杀无辜旗人,理想在 “革命的正义” 与 “人性的底线” 间撕裂。刘楚昕用近乎残酷的笔触写道:“每一次看似挣扎向上的努力,都可能因为一个微小的变故、一次人心的叵测,甚至仅仅是时代车轮扬起的尘埃,而重新跌落。” 这里的 “泥潭”,早已超越物理空间,成为旧价值已碎、新价值未立的精神困境—— 就像书中那部 “未完成的同名作”,编辑越是想拼凑真相,越发现历史的真相本就是破碎的、矛盾的,如同泥潭中捞不起的月光。
也许生死就是一场大梦,也许我正做着一场持续百年的大梦
亡灵恒丰的这句独白,道破了小说最精妙的叙事诡计。刘楚昕打破线性时间,让恒丰的记忆在 1912 年的死亡现场与清末的家族往事间闪回:前一秒还是 “右下颌骨碎了,下巴歪在一边” 的尸体,下一秒却回到 “摸黑穿过树林,树干像巨型守卫团团围住” 的少年时光。这种意识流写法,恰是对 “历史记忆” 本质的隐喻 ——记忆从不是按时间顺序归档的文件柜,而是由创伤驱动的碎片化闪回,是一场醒不来的大梦。
小说中,类似的 “梦境感” 无处不在:关仲卿在日本留学时,因陈天华蹈海事件顿悟革命理想,却在回国后发现 “革命阵营比官场更浑浊”;性别错位的 “奇人” 重返荆州,发现曾经的街道 “既熟悉又陌生,像被水泡过的旧照片”。这些人物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:当身份、信仰、时代都在崩塌,“我是谁”? 刘楚昕用哲学博士的敏锐给出答案:生死如梦,但梦中的选择真实可感。就像恒丰最终接受死亡,却在意识消散前想起妹妹的笑脸 ——即便一切是梦,那些爱过、痛过、选择过的瞬间,已是对 “存在” 最好的证明。
通过书写,他的传奇像上了油的锁头那样打开了
作家东西的这句评价,点出了《泥潭》最深刻的 “救赎”:书写本身。小说中有一个 “书中书” 的结构:编辑在混乱的文稿中拼凑 “未完成的《泥潭》”,这个过程恰似刘楚昕自己与痛苦的对话 —— 女友去世后,他在遗物中发现信笺:“希望你在痛苦中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。” 于是,写作成了他的 “锁头钥匙”:50 万字初稿删至 13 万字,从 19 世纪现实主义笔法转向现代派技巧,最终让亡灵开口、让编辑猜谜、让 “奇人” 缝合,完成了对历史中 “无名氏” 的命名。
这让我想起书中马修德神父的日记:他记录下恒妤的苦难、关仲卿的挣扎、八十四的笑,那些被正史遗忘的 “蝼蚁众生”,在泛黄的纸页上获得了不朽。刘楚昕在重庆分享会上说:“文学最核心的价值在于表达对世界和人类的爱。” 当他写下 “迷失在黑夜中时,不妨抬头看看星空”,既是对小说人物的劝慰,也是对自己的告解 ——写作无法改变历史,但可以让那些在泥潭中沉没的声音,被听见;让那些在黑暗中闪烁的良知,被记住。
合上书页,漓江的雨仿佛还在下。刘楚昕说,女友去世后,他常在深夜写作时听见隔壁房间有翻书的沙沙声 —— 那或许是虚构,却也真实:当《泥潭》的销量突破 50 万册,当读者在恒丰的亡灵独白中看见自己的迷茫,当 “面对良知” 成为无数人手机备忘录里的句子,那些曾经的痛苦,真的变成了 “传奇”。
而这,或许就是文学最温柔的力量:它让我们在历史的泥潭中,辨认出自己作为人的轮廓;让我们相信,即使身处黑夜,只要抬头看看星空,良知的光,就永远不会熄灭。
- 感谢你赐予我前进的力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