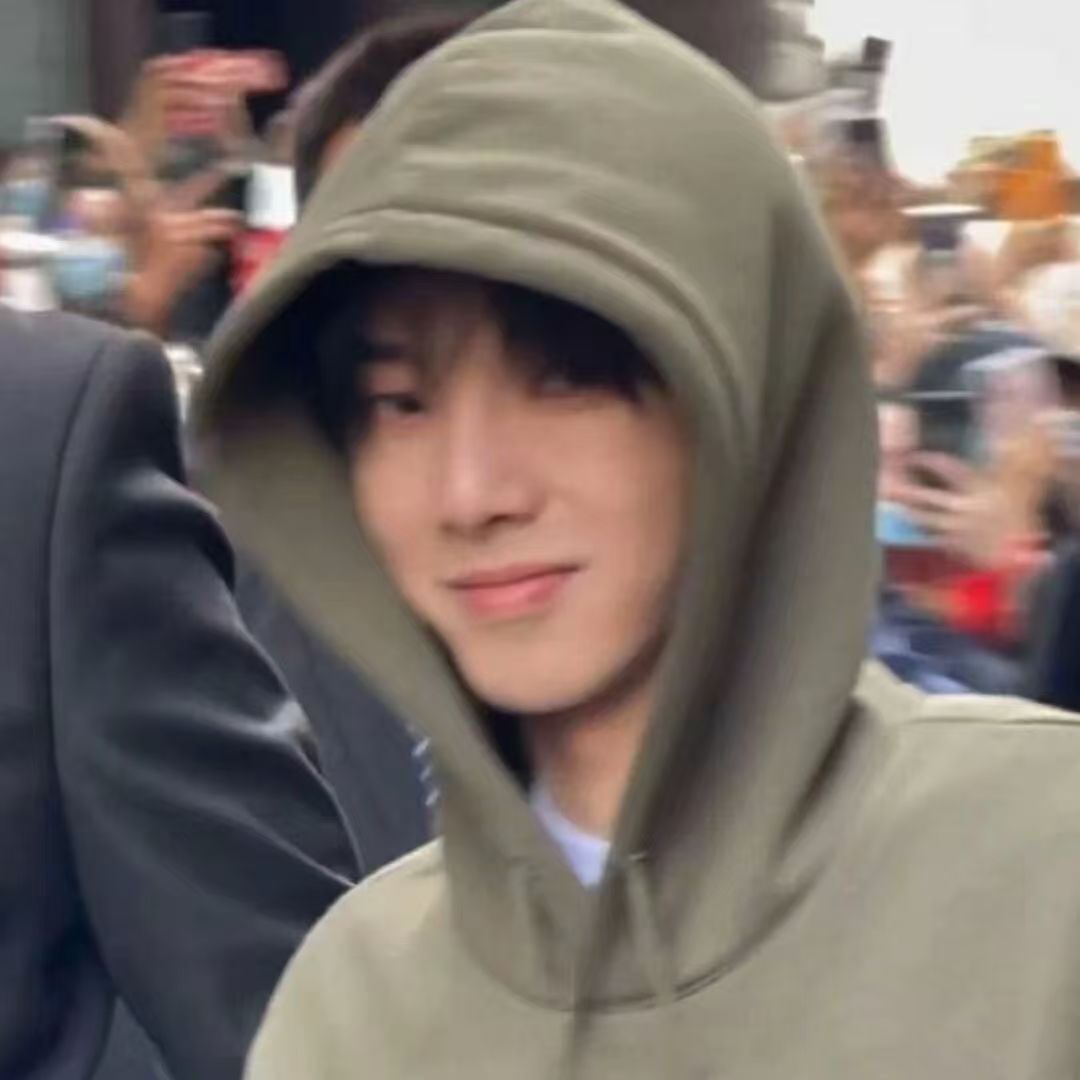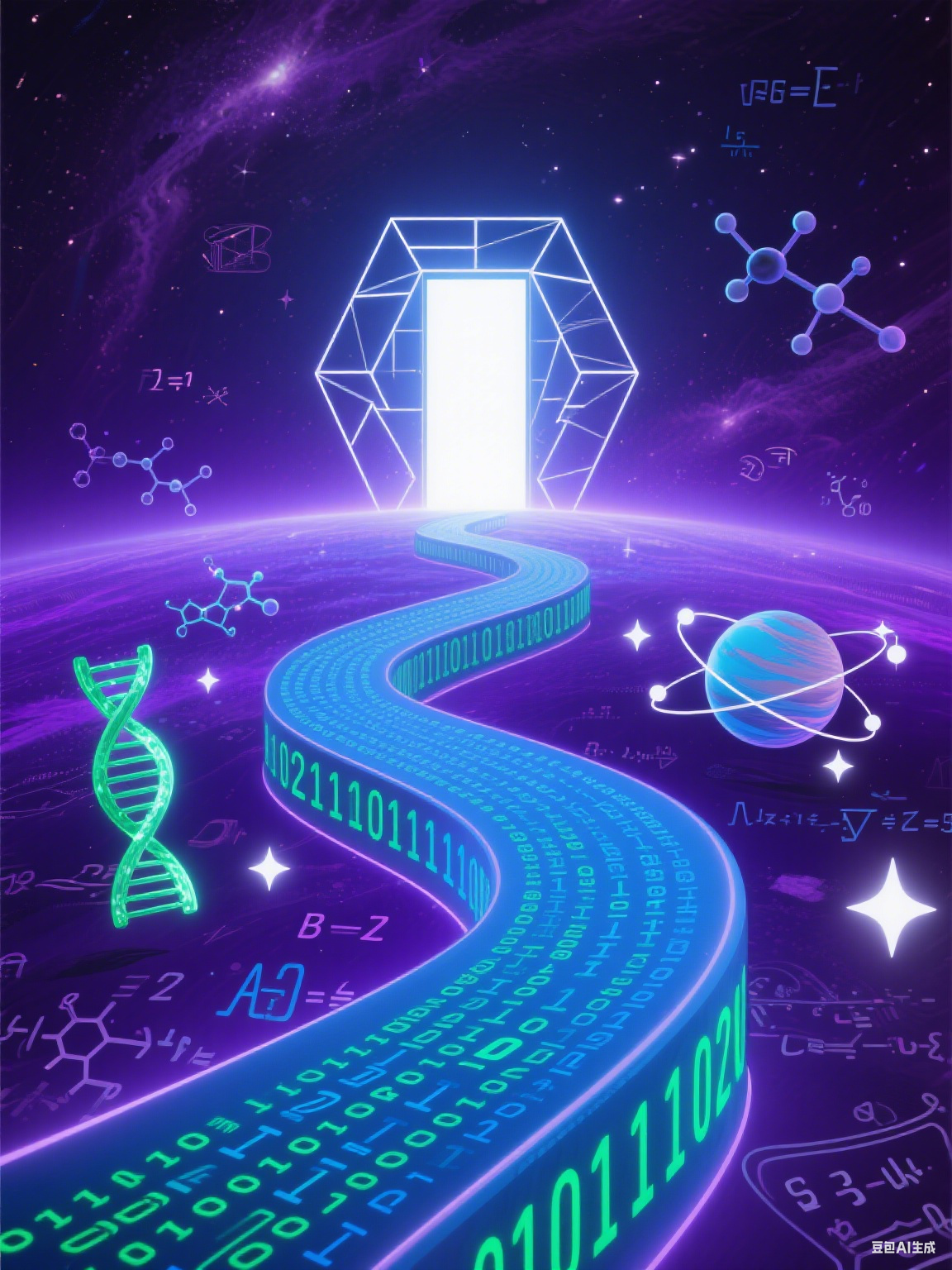
在算法与星辰之间:杨立昆的科学之路
1987 年 12 月的巴黎实验室,雪花在窗外旋转成模糊的光斑。40 岁的杰弗里・辛顿把马克杯重重磕在实验台上,苦涩的笑声在空荡的房间里回荡:"今天是我生日,我的职业生涯也到头了。" 年轻的杨立昆看着这位后来的深度学习先驱,突然明白 —— 科学的道路从来不是线性的代码,而是在迷雾中反复调试的梯度下降。
低谷期的梯度下降
在人工神经网络被讥讽为 "炼金术" 的年代,杨立昆的 LeNet 项目像一颗被遗忘的种子。当主流 AI 研究者涌向符号主义的康庄大道时,他却在反向传播算法的崎岖小径上独行。"当时我们提交的论文,评审说这是 'unscientific balderdash'(不科学的胡言乱语)。" 多年后他在访谈中轻描淡写,但泛黄的拒稿信上仍能看见 "神经网络已死" 的猩红批注。
最艰难的 1995 年,AT&T 突然裁撤整个 AI 部门。当保安收走他办公室钥匙时,杨立昆正调试着卷积层的参数。"我抱着服务器硬盘走在雪地里,突然想起辛顿那句话 —— 困难之处正是价值所在。" 这个场景后来凝结成书中最动人的注脚:"特立独行,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,即便那件事在短时间里不被人看好。"
超越语言的智能图景
在 Meta 的 AI 实验室,杨立昆常向访客展示两段视频:一段是家猫精准跃上皮箱的慢动作,另一段是最先进机器人笨拙地撞倒花瓶。"猫能规划路线,理解物理世界," 他按下暂停键,"而我们的大语言模型,即便读完整个互联网,也不知道杯子会滚动。"
这种认知鸿沟指向他最深刻的洞见:"我们不是用语言思考,我们是用对情境的心理表征来思考的。" 书中那个震撼的数据至今仍在 AI 界回响:"一个四岁孩子通过视觉接收到的数据量,与最大的语言模型通过文本接收的数据量相当。但阅读这些文本需要几十万年。" 当业界沉迷于参数规模竞赛时,他却提醒:"智能的本质是理解,而非记忆。"
开源世界的康庄大道
2025 年的北京 DeepSeek 实验室,年轻研究者们正基于杨立昆开源的 ConvNeXt 架构进行创新。这个场景完美印证了他十年前的预言:"DeepSeek 的例子表明,中国人并不需要我们。他们自己就能想出非常好的点子。" 在《科学之路》最具警示性的章节里,他警告:"如果只有三家公司控制 AI,那将是民主的终结。"
这种信念源自贝尔实验室的教训。当年他们发明的数码相机技术被束之高阁,最终让柯达破产。"开源就像神经网络的激活函数," 杨立昆在斯坦福演讲时比喻,"多样性才能产生全局最优。" 如今 Meta 的 FAIR 实验室坚持每周开源代码,那些流动的字节里,藏着他对科学最纯粹的理解:"信息的自由流动,就是进步的动力。"
未完成的梯度下降
孤凉峰的雪线每年都在移动,就像科学的边界。当杨立昆在 202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礼上谈及 "AI 仍不如猫" 时,台下响起会心的笑声。但他眼神突然锐利:"真正的危险不是超级智能,而是我们停止提问。" 这句话或许是《科学之路》最隐秘的金句 —— 在算法与星辰之间,永远保持那个 40 岁仍在调试神经网络的赤子之心。
书的最后一页夹着张泛黄的便签,是 1987 年那个雪夜辛顿留下的:"明天继续?" 杨立昆的回复墨迹已晕开:"直到收敛。" 这两个字,或许是对科学之路最好的注解 —— 不是抵达终点,而是永远在逼近真理的梯度上。
- 感谢你赐予我前进的力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