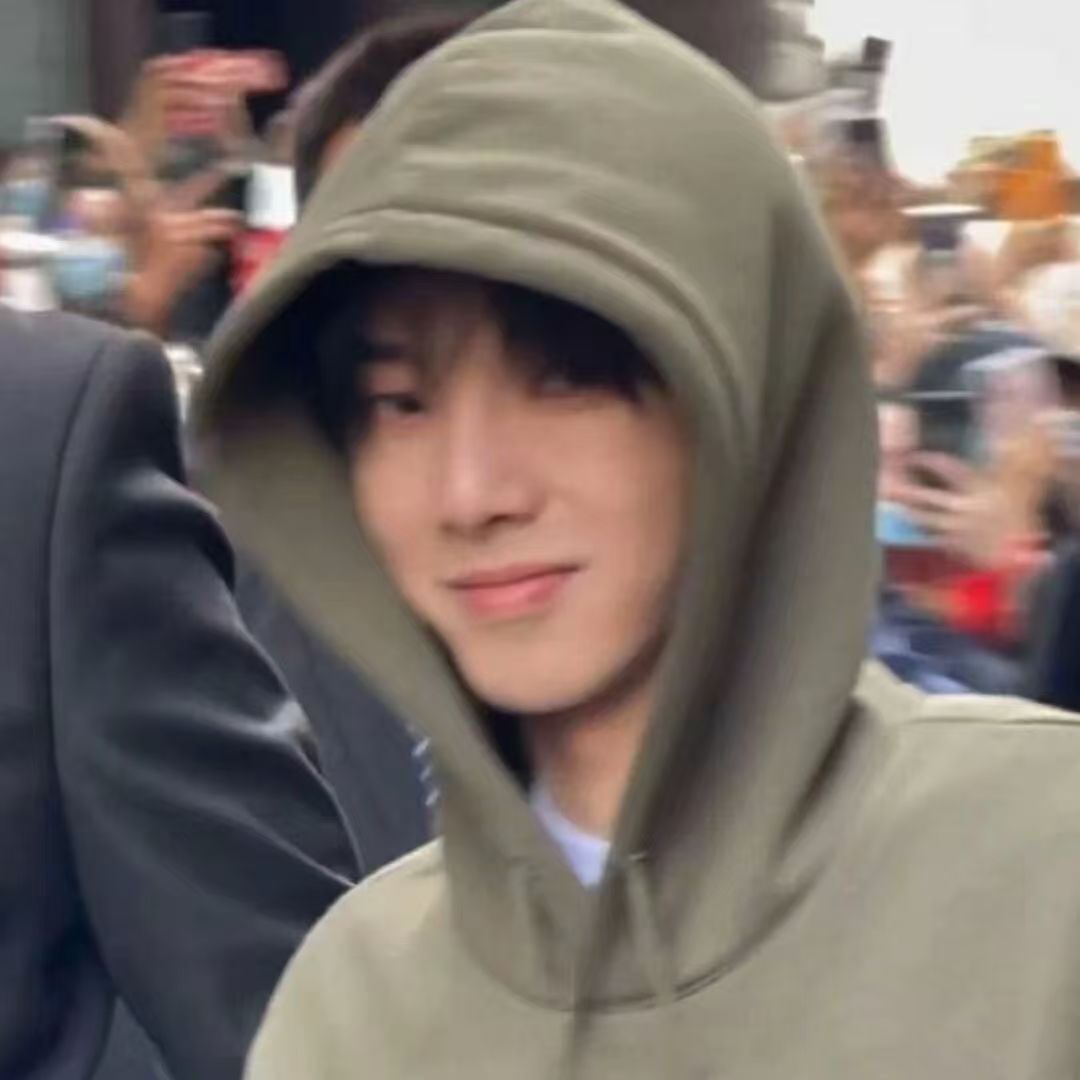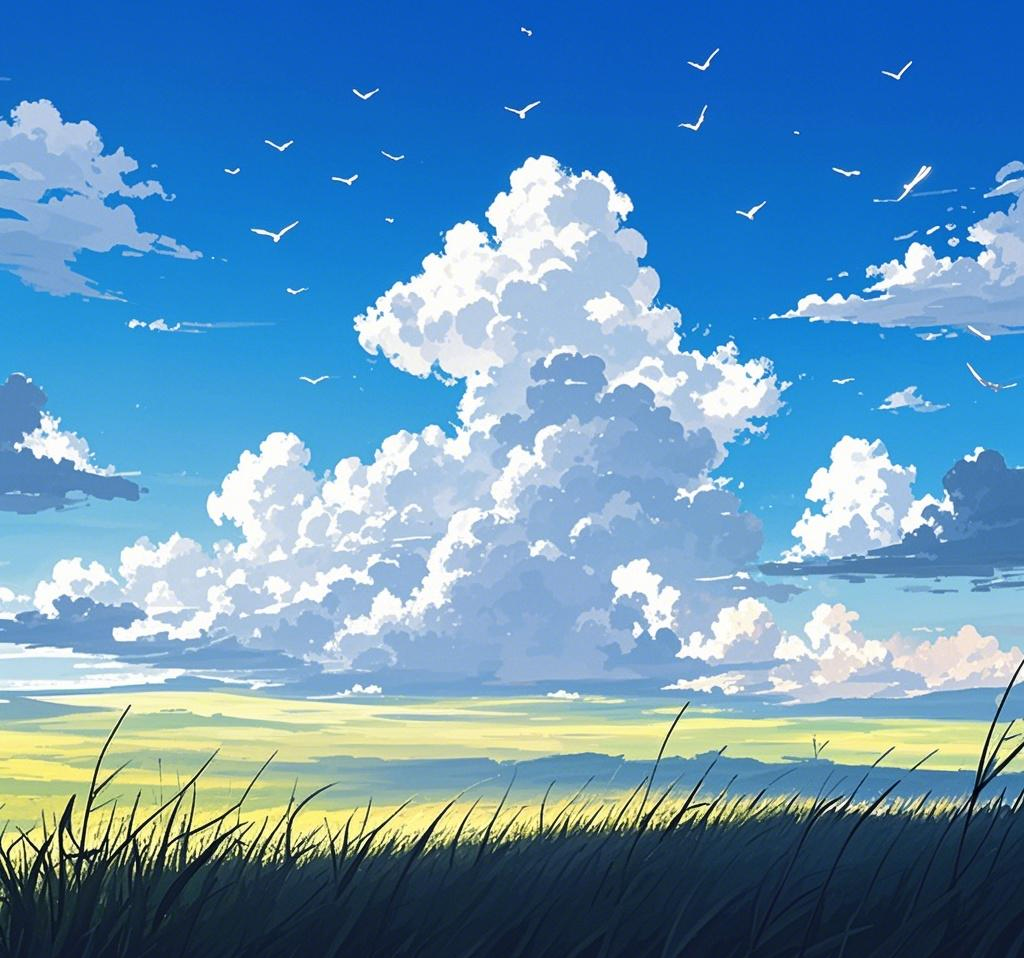
爱情,是追风还是等风来?
大二那年的雨季,走廊尽头的男生总爱把湿漉漉的伞斜靠在美术教室门边。他的白衬衫其实是泛黄的旧校服,第三颗纽扣摇摇欲坠,袖口沾着斑驳的丙烯颜料。我常在素描课时偷看他用左手写诗——那本起毛边的《里尔克诗选》里夹着食堂的餐券,墨迹在雨天氤氲成蓝色的雾。
他并不知道,他随手扔在画架旁的速写本,成了我每日午休的圣经。我用解剖石膏像的严谨,记下每处铅笔涂改的痕迹:被划掉的"鸢尾"改成"夹竹桃","鸽群"涂黑成"乌鸦的骨殖"。当他在校刊发表《致无名河流》时,我正蹲在实验楼后的水沟边,试图从锈铁管滴答的水珠里,打捞他诗中"银色的呜咽"。
平安夜那场大雪暴露了所有秘密。我攥着攒了三个月的家教费买的绝版黑胶,却看见他踮脚把唱片塞进播音社学姐的储物柜。他的手指关节冻得通红,像他诗里写过的新年灯笼,在昏暗走廊里明明灭灭。那张《月之暗面》终究没能送出去,在暖气片上烤化的雪水浸透了封套,把心形便签泡成模糊的墨团。
追求“自己喜欢的”,像在荒野里种玫瑰。你翻山越岭寻种子,昼夜不息挖土浇水,但花期未必如约而至。那些心动的瞬间、辗转的夜晚、小心翼翼的试探,最终可能只换来一句“抱歉”。可即便无果,有人仍甘之如饴——因为玫瑰未开时,你已见过荆棘上的露珠,听过风穿过花瓣的私语。
后来,我遇到一个总在图书馆等我的人。他知道我喝咖啡不加糖,记得我论文截稿的日期,甚至在我感冒时默默放一盒药在桌角。我像站在屋檐下躲雨的人,伸手就能触到递来的伞。可当我试图说服自己“被爱更轻松”时,心底却泛起一丝不甘:这场雨若永远不停,我是否甘心一生困在别人的伞下?
选择“喜欢自己的”,像住进一间精装修的房子。家具齐全,窗明几净,连拖鞋都摆在最顺手的位置。可你总忍不住想砸掉一面墙,看看后面是否藏着星空。安全的爱让人免于颠簸,却也让人在日复一日的妥帖中,逐渐遗忘心跳的震颤。
某次旅行,我在西安的城墙下遇见一对老夫妻。丈夫举着相机追拍落日,妻子提着水壶跟在后面唠叨:“再拍天就黑透啦!”他回头笑骂:“急什么?当年追你时不也等了三年?”那一刻我突然明白:爱情从不是单向的追逐或静候,而是两股风的交织。
真正的爱,会让“追风者”学会驻足,让“等风者”生出勇气。就像山涧与巨石——溪水奔涌时,石头是阻碍;但当它们彼此冲刷经年,石上会留下蜿蜒的纹路,水中会沉淀星辰的光泽。你或许曾为某个背影奋不顾身,或许曾被某份温柔轻轻托住,但最终让你扎根的,一定是那个让你同时看见自己与远方的人。
爱情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。它更像一场即兴舞蹈:有时你主动伸手,有时你跟随旋转;踉跄时不羞赧,合拍时不狂妄。若非要一个答案,或许是——去爱那个让你在追逐时仍能自洽,在停泊时仍想生长的人。
毕竟,最好的风,从不在意谁先动了心,只在乎能否共写一片云的形状。
- 感谢你赐予我前进的力量